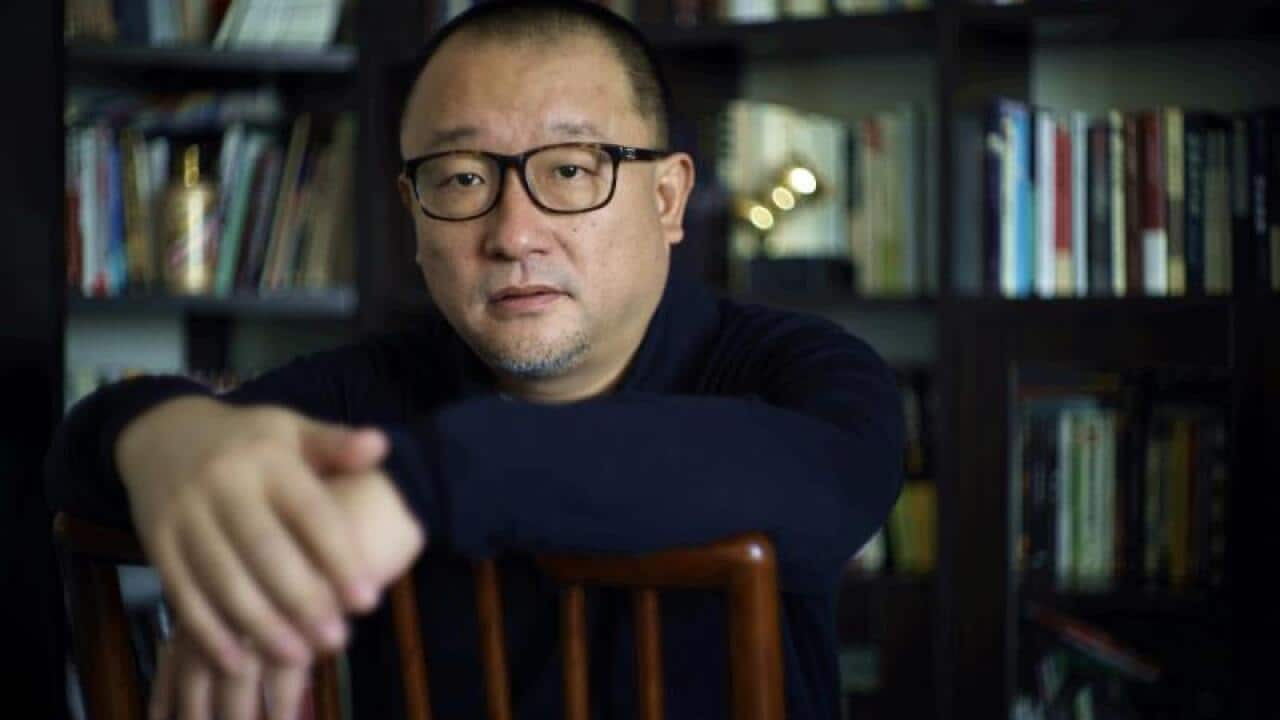在长达三年的新冠疫情消退之后,墨尔本仿佛逐渐恢复到了疫情前的热闹,各类国内、国际的文化、戏剧演出、交流不断,我们很高兴能与近来来澳访问、演出的中国戏剧导演、新浪潮戏剧运动的发起人王翀面对面地对话。
LISTEN TO

【专访】王翀:从《阴道独白》到《中国制造 2.0》 从新浪潮戏剧到线上戏剧
SBS Chinese
04/05/202346:09
王翀上一次在墨尔本的演出访问是2017年的《小皇帝》,当时王翀与澳大利亚知名编剧拉克兰·菲尔波特(Lachlan Philpott)合作探讨了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
请问王翀在时隔近六年之后再回墨尔本演出,是怎样的感受?反响如何?
王翀:上一部是2017年的《小皇帝》,在Asia TOPA演出,但是场地和出行方都是Malthouse Theatre,我叫它酿酒厂剧院。这一次做Made In China 2.0),其实因缘也是有这两个机构的合作,2020年又有一次Asia TOPA,酿酒厂剧院又出品了《中国制造 2.0》的试演版本,2020年年初,我就在墨尔本,在疫情发生之前,我们就创作这个戏,进行了三场的试演。之后有很多事情发生了,我就回国了。去年年底又来到墨尔本继续这个戏的创作,把戏做完、形成了一个55分钟的版本。今年,我们去了波士顿做首演,然后又回到墨尔本继续演出,所以一共演了33场刚刚结束。
《中国制造 2.0》是您的个人表演,这个作品的灵感是什么?这个作品被描述为剧场、单口喜剧和纪录片的混合体,您为何采用了这样的表达形式?
王翀:是,其实我一般都是那个躲在幕后的“阴险”的导演,是一个谋划的人、一个指挥的人、藏在黑暗的角落中偷偷笑的人。这一次自己把自己放到舞台上、编导演于一身其实是有几重的考虑,有一个墨尔本的同事叫Emma Valente,担任联合导演和设计师,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还有一个叫Mark Pritchard,是戏剧构作,相当于是军师和参谋,其实是我们三个人的团队。
当然是基于一个现实问题,就是预算有限,那就最好就自己上,加上我人近中年,我需要讲述一些自己的经历、自己家庭上的、职业上的、如何看世界。其实以前我做导演都是基本上我不做编剧,基本上我也不用上台演出,有个别的演出时,我在自己戏里演一个小配角或者演我自己、作为导演出现在舞台上。但这一次完全不一样,这一次我依然是作为导演出现在舞台上,但是我讲的都是我自己的故事、我亲身经历的一些东西。
所以它是一次巨大的冒险,因为你要把自己的脆弱、自己的悲剧、自己的可笑的地方,全都放在舞台上跟大家分享。
比如说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其实我是很不愿意在创作中分享的,是会跟同事分享的,是有些创伤的经历。但恰恰,我的同事认为这些东西是最有趣的,所以经过心理上的疗愈式的创作之后能够克服这恐惧,把这些内容放到舞台上。
这是您第一次作为一位演员在舞台上且一个人单独表演吗?
王翀:其实以前也演过戏,比如说在林兆华导演的戏里演蒋雯丽的一个仆人,也是一个大戏里有台词的角色。但是,那个时候我只有20多岁,我演一个80多岁的老奴,到了现在,我演41岁的自己,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根本就不是一种戏剧。
《中国制造 2.0》不是再现什么样的场景,就是当下的我直接面对观众,此时此刻,2023年,王翀面对墨尔本的观众,有很多的笑话是开给自己的,有很多的笑话是开给观众的。
形式上的创新,其实并不是说独角戏或者自编自导自演,这些内容其实前人都做过。具体到我们这个舞台上,我们做了很多的即时影像、现场的影像,通过数字的剪辑和编排跟现场的表演发生关系。
我们也用了即时的录好的影像,我们也用了增强现实AR,我们也用了3D打印,其实这些手法都可能是前无古人的或者说极少的在舞台上使用的手段,尤其是增强现实和3D打印。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虽然是一个预算极小的东西,但是它是汇集了几个同事的冥思苦想,也经历过跨度三年多的创作时间,我们有时间去回味、有时间去反省,甚至2020年还带着观众演了三场,再去增加内容,所以这是打磨出来的一个作品。
未来一段时间在澳大利亚有何演出和创作计划?
王翀:十月底阿德莱德澳亚艺术节(OzAsia Festival)会邀请我们演出一周。今年或是明年,我们有悉尼、更多的澳大利亚的城市的计划。在墨尔本,我希望明年年中能够带来一部新的作品,是我的下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它是关于我拍摄一个纪录片,那个纪录片是关于一个已经自杀的导演。

Wang Chong_Made in China 2.0 Credit: Tamarah Scott
事实上,王翀进入戏剧行业前念的是法学,您是如何走上戏剧之路的?
王翀:引用我在《中国制造 2.0》的一句台词,“我从中国最优秀的法学院学到的最大一个收获就是我想做戏剧”,其实就是因为还是有颗文艺的心。在高三时就想去北京电影学院学电影,但是当年正好没有招导演,我考中戏也考上了,但是我当时不懂戏剧、也不懂影视,最后同时也考上了北京大学的法学,我最后还是去学法学了。学法学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还是文艺的心放不下来。所以大二、大三的时候,我就开始大量地看戏、看电影,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选的课都是以艺术课为主,因为主课都已经修得差不多了。其实还是遇到贵人,当时有一个夏威夷大学的博士生、台湾学者林伟瑜,我跟他在北京遇到,他算是诱导我,说你也可以去美国念书,你也可以跟着林兆华去尝试做戏剧、给他做助手。所以这两件事我就都干了,我给“大导(林兆华)”做助手的过程当中研究他的作品,发现这个东西是表达足够深邃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后来也去申请美国的学校,最后去了夏威夷大学念了硕士。
回国后从草根戏剧或者说独立戏剧做起,我2008年回国成立自己的剧团,2009年一下做了三个作品,第一个作品其实就是《阴道独白》(The Vagina Monologues),这就算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了。算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时正好赶上国内的各大青年戏剧平台或者说独立戏剧平台“雨后春笋”般的爆发了,我们等于是搭上了这一班青年戏剧平台的托举。说白了,青年戏剧平台就是意识到国有院团其实已经无法担任创新甚至引领市场、探索艺术前沿的这些作用,它们跟真正意义上的观众和时代有些脱节了,所以基于这个现实,越来越多平台,其实大多数都是接受国家资助的,他们愿意资助年轻人、独立戏剧人去做新的戏剧艺术。
2009年您推出《阴道独白》是在中国大陆的授权中文首演,这部由美国女作家伊芙·恩斯勒(Eve Ensler)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创作的当代女性主义经典名剧反对家庭暴力、呼唤男女平等,唤醒全社会对女性的尊重,当时在中国各大院校、戏剧社团引发不小的反响。请跟我们介绍下当时您所翻译的这版大陆中文首演的情况吧。
王翀:说起《阴道独白》的历史,最早它是1995年纽约的一个独角戏,是一个自编自演的、由伊芙·恩斯勒做的戏剧,它基于对200多位女性的采访,加上她自己亲身的受性暴力的故事,把200多个采访集结成了九个故事、搬上舞台。1995年伊芙·恩斯勒做了这个戏一炮而红,1996年获了外百老汇的奥比奖(Obie Awards),到了零几年的时候,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做了中国大陆第一个的演出,但是一个内部的没有售票的演出。后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曾经做了自己的版本,但是没有公演就主动地自我审查下架了。所以,这才等到了2009年由我这样一个独立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一个人去做了自己的版本。自己的版本是指自己的译本,因为根据授权你没有资格去添加自己的内容。
我当时找了三个演员,一个是台湾人、一个是美籍华人,还有一个是大陆人,她们也很勇敢,跟我一起做这个戏。当时第一版翻译还是非常稚嫩的,在我们巡演三十多场的过程当中,我们去不断地打磨翻译、变成一个特别接地气的语气通顺的作品。一开始我们在北京朝阳区的九个剧场演出,其实还是有点秘密会社的性质,因为当时是公开售票了,但是没有在传统平台上公开售票,是一个新兴的网络平台,那一轮五场演出其实没有经过审批,那是因为剧场方骗了我,说我帮你去审批,其实到最后也没有敢提出审批,出于保护我的目的说可能觉得不审批也就能混过去了,所以等于是帮着我连哄带骗进行了一次非法的售票公演,那是2009年三月。
几个月之后,我们在北京的另外一个剧场进行了合法的、有演出许可证的售票公演,那是一个更加的让我振奋的(演出)。因为之前有艾小明老师的版本,但是那个版本局限于一个城市,并且没有这种非常正式的合法化的通过官方公开售票平台的演出。
我觉得这种亚文化其实具有巨大的爆发力,如果你能把它带上这种经过审查的合法平台,可能会迸发出巨大的社会反响和象征意义。
因为原来《阴道独白》这样的东西、带着观众在舞台上、在剧场里一起喊“阴道”这个词,表演几十种不同的呻吟方式、表演被性侵的人是如何治愈自己、走向新的生活、新的对身体的认知,这些东西放在一个合法的公开平台上,它对人的那种启示作用其实更大,它不再是一个秘密会社、小圈子,而是所有公民都能共享的一个文化的果实,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我们之后巡演了五、六个城市,三十多场,这里有一半以上的演出都是合法的,我是特别地自豪。

Wang Chong_Made in China 2.0 Credit: Tamarah Scott
王翀:准确地说,因为我们这个版本巡演的例子,《阴道独白》后来在中国一些其他城市也有过合法化的例子,但是确实不是在所有城市都能够合法公演。当然,某种程度上我能理解,因为我们中国其实还是处在转型期,从八十年代开始到现在还没结束,我们还在非常努力地朝着文明的、开放的、国际化的社会去转型,《阴道独白》是转型当中的一个标志物。
其实,你看这个戏在西方接受的过程也没有那么一帆风顺。1995年首演的时候,作者认为这个戏八成又是一个失败、事业又会走向一个新的低谷,她自己演出之前也是非常忐忑的,无法预测这个戏能够一炮而红。之后,这个戏在美国演出的时候也受到了阻力,比如说,有些教会学校的学生想在校园里演,学校就不让,这些学生只能说第一是抗议,第二是在学校旁边的社会建筑里找一个空间、自己演出,依旧请自己的同学和老师还有社会上的朋友来看。伊芙·恩斯勒也去了那个学校、加入讨论,跟校方进行交涉和沟通。其实在美国这样一个所谓的民主和自由的世界里,依然是有可能遇到来自民间的阻力,注意不是政府的阻力。
我们也看到《阴道独白》成为了那一、二十年全世界范围内演出次数最多的一个戏,全世界大学校园包括中山大学的艾晓明老师都在做这个戏,社会上的商业演出、巡演也都在全世界发生,有一个记录是它已经在140、150个国家演出过了。所以,当时其实我做这个戏的时候,我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凭什么一个戏在140个国家演出过,在我们中国就不能演出?我就一定要让它合法演出。当然,我发这个口号的时候,我其实也不确信百分之百能,但是你不试你怎么知道呢?
时至今日,在中国我们看到了关于女权或者女性主义的大量探讨,很多勇敢的女性站出来去挑战固有的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您觉得这部戏剧在当下中国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王翀:是,一方面是教育,一方面是女性主义的觉醒,还有一方面也是促进两性沟通。因为《阴道独白》不仅仅讲的是女性的自我认知、被性侵之后的疗愈,也包括能够欣赏女性的男性、能够帮助女性成长的男性的故事。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女性自己特别羞于正视自己的阴道,觉得自己的阴道是世上最丑的东西,但是她遇到了一个男朋友,那个男朋友特别喜欢看她的阴道,把它当成一幅能够注视一两个小时的油画去欣赏的这么一个事物。这种来自男性的凝视,你可以说有政治不正确的成分,但是这样的男性是有可能帮助女性达成两性的和谐相处,重新去除羞耻、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的。
《阴道独白》不仅仅是在中国有价值,在世界各地其实就算是再开放、再进步的(地方),其实也需要由《阴道独白》来提醒我们,我们依旧有很多禁忌施加在证明一个正常不过的又是非常伟大的人类器官上,同时在中国,那就更是如此。在中国,女性主义最近这十年其实是特别地蓬勃发展,也受到了很多阻力。
其实我希望《阴道独白》能在中国永远地演出下去,不断地传播这样的理念,让更多人加入这种走向未来的性别觉醒的行业里。
2012年,您和您的同事一起发起了新浪潮戏剧运动,还发表了一份《新浪潮戏剧宣言》,能否请您介绍下当年发起这一运动的契机? 十一年过去,如今您会如何看待这场运动?
“我们——我和我的朋友们彻夜未眠。我们坐在北京的迷雾之中,听浪潮拍打着千疮百孔的堤岸,掀弄着卫道士的小船。我感到腥咸的海水扑面而来,触手可及。我想脱去廉价的衣衫,纵身跳入浪潮之中,在海水中重建这个世界。 ” (《新浪潮戏剧宣言》)
王翀:其实当时有一个特别简单的、狂傲的想法,就是中国戏剧太差了,我们需要做更好的戏剧,我们需要做更新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新浪潮是一个特别有力量的象征,这也是我当初做戏剧的初衷。我当时学戏剧的时候就是觉得中国的戏剧不管是创作还是研究都太差了,都放在那么多未知空间没人去探索,还是陈规陋习式的保守的非常旧的戏剧美学研究范式,也是我一开始学戏剧和做戏剧时候的初衷。
到了2012年,我认为羽翼有点丰满了、可以进行更大程度一轮探索了,所以那一年做了四部长戏和两部短戏,现在看起来是有些稚嫩的,但当时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我几年前不敢想象的,在导演、表演、舞台艺术的创作上,其实是超越了几年前的《阴道独白》,把我的戏带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上,也能够对整个北京甚至中国的戏剧形成一种震撼或者一种批评式的力量,因为实验戏剧或者说前沿戏剧,它本身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此,必须有旧的事物作为一个对比,有保守、主流作为一个对象,才能够在参照系之上拉开人们对它的期待、形成震撼,其实当时是有这样一种特别强烈的立场,那年我才三十岁。
做了四个长作品包括《雷雨2.0》,后来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去到台北艺术节、以色列艺术节和纽约“雷达之下”国际戏剧节的中国大陆戏剧。
其实当时选择《雷雨2.0》,就是为了用这样一个很陈旧的、美学上已经固化了的作品,我们期待如何站立在曹禺大师的肩膀之上向远处进行一个远眺。
用的手法就是在舞台上用了六台摄影机,后来的版本里加入了评弹这样一个苏州的说唱形式,台词、拟音都是来自于评弹的乐器、艺人苏州话的唱词,但是舞台上方的大屏幕用即时影像、用舞台电影的手段,给观众一个影像化的、电影化的视觉呈现,声音上又是苏州评弹的感觉,所以它构成了一种特别诡异的、有趣的、显然不是北京人艺的那种传统舞台的作品,我就觉得挺有冲击力。
听说您将《雷雨》99%的台词都删掉重写、只保留了1%?
王翀:对,其实可以说整个故事就只保留了男女关系的骨架,以四凤、繁漪和周萍这三个人的故事和关系为主线,但是事实上台词都删得不剩什么了,只是通过影象化的表达,在舞台上用摄影机现场去拍摄,通过这种表达去解构一个新的发生在一个夜晚的男女之间的三角恋情和男性对女性的压榨这样的故事。其实是一个特别大胆但又特别合理、合法的(做法),因为我们也就这个作品付费地获得了曹禺家族的授权。包括我们后来做《茶馆2.0》的时候,我们也是等到了老舍大师过世第51年的时候进行演出,因为50年是版权保护期,到51年时,我们就是推出了《茶馆2.0》。
那个作品更加疯狂,我们其实是在中学的教室里面演出,都不是剧场,演出就在中学的教室当中发生,每场只能坐11个观众。11个观众背对着教室的窗户,面对着教室的门,左手是前面的黑板,右手是后面的黑白。每场11个观众、44个演员,44个演员里包括25个中学生、5个大学生、十几个社会上的业余演员和2个专业演员,这样的一个演出团队其实是用了可以说环境戏剧或者说非特定场域的戏剧,因为你不在剧场演出,教室本身能带给你巨大的冲击。
我们其实是在完全保留老舍台词的情况下——这就跟《雷雨2.0》不一样了,《雷雨2.0》是删掉99%的台词——在《茶馆2.0》里,我们可能也就删了1%的台词,剩下99%都是不改动的,公公就是公公,老佛爷就是老佛爷,我们是用老舍的语言夹在中学校园的生活之上。
老舍表现的是一个茶馆的没落与崩溃,我们表现的是一个中学教室的没落与崩溃。老舍的三个时代是清末、民国中、民国末,我们的三个时代是高一、高二和高三高考之后这样的叙事。所以,其实你看到的是真实的中学生演出中学生的生活,穿着自己真实的中学校服,师生之间的互动,学生跟社会上的流氓之间的对抗,就是用老舍的那种北京话表现当代北京的中学的状态。
疫情改变了很多事情、很多人的职业或想法,看到您在2017年时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停电亭”,让自己进入一个没有电、没有网络的环境中、与外界喧嚣相隔绝;而现在,你推出的线上戏剧又需要无限地依赖技术、电和网络。为何会发生这样的转变?疫情中,您推出了两部线上戏剧《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鼠疫》(Plague),能跟我们介绍下您的这项尝试和反响吗?
王翀:其实最早是在2019年的时候来澳大利亚开会,需要继续地跟同事保持联系,我们开始在线上开会,那个时候我才知道ZOOM这样一个线上通讯的软件,它远远超过传统的那些视频通话的工具,因为它能允许很多人在同一个屏幕出现,传输速度、效率特别高。首先是技术本身震撼了我,2019年当我看到25个同事同时出现在一个屏幕上的时候,我想的就是:我必须用它做一个戏——不知道是什么戏,也许是一个莎士比亚的大戏,因为有很多角色可以同时出现——但是我知道我肯定会用它做一个戏,但是什么时候做,我暂时不着急,可能2022年、2023年做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当2020年我还在墨尔本创作《中国制造 2.0》的时候,疫情就发生了,我就跟国内的同事开始用ZOOM视频,在筹划说应该做一件事情,现在大家全都居家了,我们应该做一个跟生活、跟当下、跟现实直接相关的作品,用ZOOM做线上戏剧成为了一个最直接的灵感,等于是现实把这样一个我几个月之前就发现的科技手段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艺术概念,我们推出了我们的第一部也是中国的第一部线上戏剧《等待戈多》。
这是用的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剧本,我们把它当下化,类似于《茶馆2.0》的那种手法,我们嘴上依然说的是两个流浪汉,但视觉上看到的是一对夫妻在不同的城市居家隔离,当时还是春节刚过去不久,2月是春节,3月我们创作这个戏,4月首演,所以你看到的其实场景是一个夫妻或者一对恋人,两个人都带着戒指,女的是一个人在大城市的家里,男的是在小城市的家里,他跟他的弟弟还有父母一起。两个人成天在网上同一时间上线,然后开始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在一起、我们要不然就分开算了、明天怎么办……什么明天?我昨天是不是同样都是这种感觉过来的?
贝克特大师的那种等待、那种焦躁、那种日复一日的重复、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何时、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不知道这样的状态什么时候能结束、不知道谁能来救自己、不知道那个所谓的救星戈多什么时候来、他会带来什么……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其实是高度契合了2020年初当下的中国社会的心理。
戏剧演出全部停止,我们那个其实是春节之后的第一部新戏上演,春节之后都已经快两个月的时间了,都没有新戏,因为别人没有这个概念,剧场全是关着的,没有这样一个创新的实验性的想法,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新的作品创作。其实我们针对的就是那种所有人都闷在家里、不知道武汉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自己的城市会不会下一个、不知道疫苗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国家政策是什么样……只能在这种忐忑的等待当中。
所以,很多观众后来看了之后说,他们是第一次看懂《等待戈多》,因为有一个不是那么虚头巴脑的中国演员戴着礼帽、穿着西服的演出,而是看到了接地气的中国家庭生活场景,但是台词全是贝克特的,我们是没有制造新的台词——其实是顺着《茶馆2.0》的那种创作思路,用语境、用道具、用布景、用表演产生新的情境和意义,让远在法国的流浪汉变成了在中国当下居家隔离的一对异性恋的恋人。
另外一部线上戏剧是之后推出的《鼠疫》,很多人在疫情中回看这部来自加缪(Albert Camus)的经典小说,缓解内心某种不安的情绪。这部戏剧是否主要还是在海外上演?
王翀:对,这部戏剧其实当时希望能在大陆找机构去合作,但是大家已经“噤若寒蝉”了,那个还是2020年,那都不是2022年。“噤若寒蝉”是指大家都根本不敢反映现实,根本不敢和疫情有关系,除了歌颂的作品,就没有人敢做任何别的作品。我做《鼠疫》,不是说非要批判中国的防疫政策,只是说我希望有一个更大的视野、用全球化的方式去审视我们当下的疫情。
其实《等待戈多》,我们是四个演员、在三个不同的城市进行线上即时演出,这三个城市包括北京、武汉和大同。到了线上戏剧《鼠疫》,我们就变得非常得有野心了,我希望表现的是全球抗疫的宏大图景。大陆的机构不愿意合作,那也就罢了,我们也能理解。我们就找到了香港艺术节,我就去了香港,跟香港的技术团队坐在一起,我们线上的演员是一个人在武汉、一个人的在纽约、一个人在伦敦、一个人在贝鲁特、一个人在南非、一个人在里约,六个演员是在五大洲的六个城市,还有两个设计师是在墨尔本,所以它构成了六大洲的艺术家连接在一起、同时上线进行创作排练,且演出也是即时的线上的。所以你能看到武汉的女孩远处高楼大厦的Led屏幕已经是在夜间闪亮了,你能同时看到里约和纽约的演员,那个是早上,你能看到南非的是正当午这样的时间。其实是用全球化的手段、用全球化的这演员来表现全球化的题材,其实早就超越了批判某一种抗疫政策,其实是人类如何面对灾难。
有趣的是,在剧本里,这是一个英国人改编的加缪的《鼠疫》,英国的改编版本里不像加缪,加缪提到了城市的名字,在英国的改编版本里已经没有提城市是什么名字了,只是说我们在一座城市里。但是在我们这个线上戏剧里,不仅仅是没有名字,其实你看到的是明显你不在一个城市,种族也不一样,大家在戏里主要说英语,还说了很多别的语言,说中文、说葡萄牙语、说祖鲁语、说阿拉伯语,其实是用这么多种语言,当内心独白的时候就变成自己的语言了,其实表现的就是人类到底如何经过一场瘟疫。
您认为当前最值得强有力地被表达的中国话题是什么?
王翀:我其实还真的就没有计划,因为要表达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不能表达的东西也太多了,但是好在不能表达的东西其实可能还有别的渠道,比如说《茶馆2.0》,其实是批判教育系统问题的这样一个作品,如果不能在剧场里上演,可以在教室里上映,在不售票、不通过审查的方式上演。戏剧是一门活的艺术,所以其实具有很多的空间。
我最直接想到的是在中国大陆,我相信女性主义议题其实是能在戏剧里有巨大的这种可能性的,最近也涌现了很多优秀的女性戏剧人,依然是大有可为。
具体到我身上,我会今天去意大利进行我以前的一个作品《我们从何处来2.0》的意大利语版本的创作。之后四个月,我会去挪威进行一个纪录片的后期创作。之后我会进入新的两部作品的创作和排练当中,希望两部作品都有机会在2024年来到墨尔本。
欢迎下载应用程序SBS Audio,关注Mandarin。您也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等播客平台随时收听和下载SBS普通话音频故事。请在 和 关注SBS中文,了解更多澳洲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