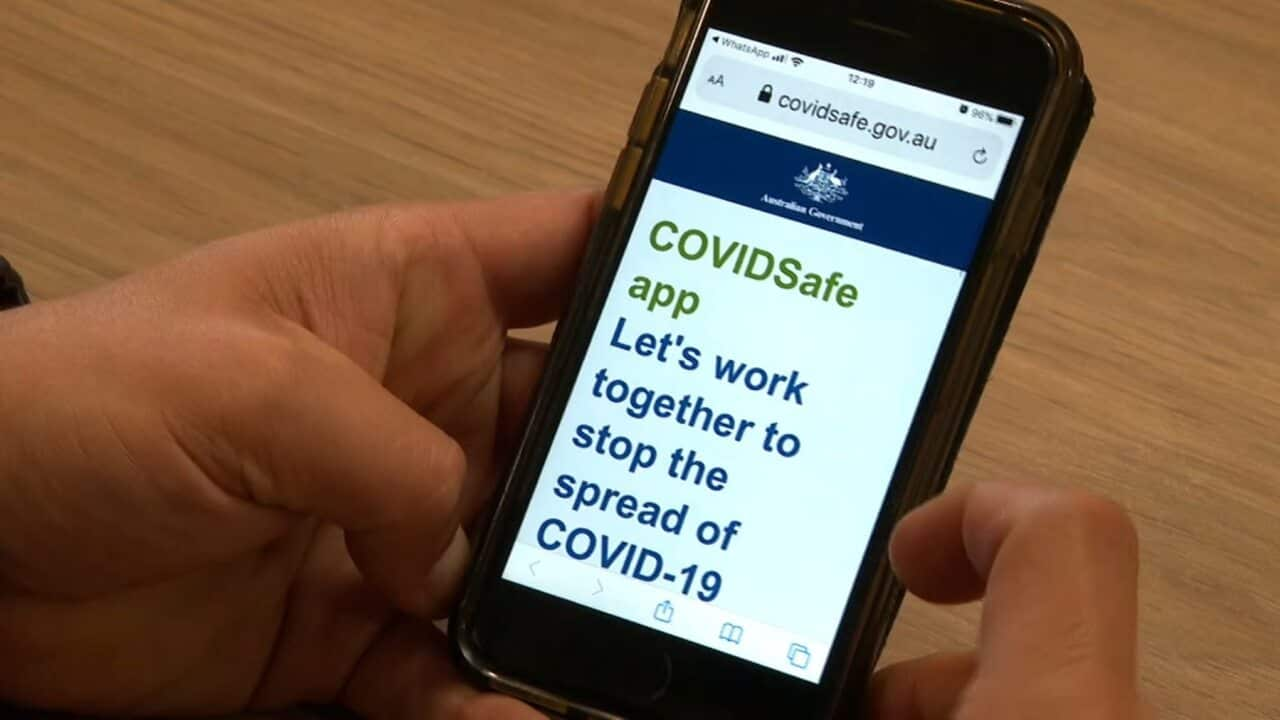在我的高中年鉴里,有一张我大睁着眼睛满脸笑容的照片。那张照片很完美——我上的是一所男子私校——当时我穿的是一件深蓝色、镶有金边、装饰有徽章和各种符号的休闲西装校服。这些标志意味着我是这个以有钱白人小孩为主的群体的领袖。
拍照那一年早些时候,有一次我因为某件事而在笑,就在我正开心的时候,我听到几个白人朋友说:“尤金,笑的时候把眼睛睁开”。我回家后对着镜子笑,然后发现我的亚洲眼几乎看不到了。
于是我听取了我朋友的建议。在那张完美的照片中,我试着让自己看起来像是我以为我是的那个人,也就是那个让我如此自豪的“领袖”。我刻意把眼睛睁大了。
当年在那个充满种族主义的时刻让我睁开眼睛的那几个白人,现在却在Instagram上向我宣讲种族主义的问题。他们去参加了抗议游行,分享了各种资源教人如何支持这项运动。他们为明尼阿波利斯警局资金来源被砍的头条新闻而庆祝,又因为爱德华·科尔斯顿(Edward Colstan,17世纪英国商人、奴隶贩子)的雕像被扔进英国布里斯托的雅芳河中而大笑。
我也试着像他们一样为此而欣喜,但我做不到。如果这个运动向我揭示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我自己已经变得多么愤世嫉俗。
是个用来解释为什么白人不擅长讨论甚至不愿去思考种族主义的概念,因为这么做会让他们感觉很糟糕。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会通过各种行为来逃避这一话题,比如否定种族主义的存在、在别人提出种族主义指控的时候勃然大怒、或者在有人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退出对话。
我很害怕。因为愤世嫉俗的我现在只能把那些参加游行和在社交媒体上支持这场运动的白人看作是白人脆弱性的最新表现:他们没有直面自己过去或将来可能出现的种族主义行为和想法,而只去追求推翻种族主义的制度和体制,因为这么做更令人振奋和激动,不需要令人痛苦的反省。
承认我们自己的种族主义言行非常困难,而且没有人能看到,这让我觉得很伤心。而且由于我的愤世嫉俗,我甚至不敢去希望有人在这么做。 但我懂。自己有可能是或者曾经是一个种族主义者,面对这种想法或者接受这种想法是非常恐怖、丑陋和艰难的,因为这是我们对自身期待的最大背叛。
但我懂。自己有可能是或者曾经是一个种族主义者,面对这种想法或者接受这种想法是非常恐怖、丑陋和艰难的,因为这是我们对自身期待的最大背叛。

种族主义的基础是仇恨、愤怒、怨念、尖刻,还有其他直接和我们所信奉的价值观相矛盾的感受。把这些东西从我们自己身上完全剔除,投射到别人身上,这么做是最简单的。承认我们自己有可能偶然间表现出种族主义相当于承认我们不是我们眼中的自己,也不是养育我们的家人、最亲爱的朋友和爱人、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眼中的我们。
直面我们自身的种族主义非常艰难,非常痛苦,因为这么做会摧毁我们对自己的认识。
但是许多非白人族裔却不得不这么做,仅仅是为了能不在已经内化的种族主义和自我憎恶的压迫下生活。我内心中就有一部分深深憎恨我眼睛的形状,恨不得把它们撕开。
显然,我并没有真的这么做,但这种憎恨撕裂了其他很多东西。首先被撕裂的,是我曾经是“白人”,或者有一天可以成为白人,最终完全和他们同化的想法。然后被撕裂的,是我曾经拥有的归属感、我对我朋友的信任以及对于陌生人的信任。
然后是我对未来的期盼,在这个世界中,我永远会是一个外人。
我把曾经的骄傲丢入黑暗,但我也将过去的一些羞耻拉到光明之下。在这些我曾经有过的羞耻感中,我现在却可以看到很多美好,比如我的家人,我们的食物,我眼睛的形状,我皮肤的颜色,以及其他同样被当做外人的族裔的文化和肤色。
最出人意料的是,我对自己的歧视和我对其他人的歧视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像是我所憎恨的我自己的一部分一样,不是白皮肤。
许多在西方社会长大的非白人族裔的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心路历程。他们不得不把自己撕裂、剖开、分解成碎片,只是为了能从“同化”和“融入”的枷锁中挣脱开来。
一部分的我觉得很愤怒,因为我感觉能有这场运动的反思要感谢我们。如果白人支持者们想要给我——或者说我们——上课,他们至少需要自己经历过这种痛苦的反省才有资格,但我甚至没有勇气来心怀这个奢望。
詹姆斯·鲍德温(美国作家、社会活动家)给我提供了些许慰藉。他曾说过,如果“融合”这个词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话,它应该是这个意思:“我们带着爱,强迫我们的兄弟们认识到真正的自我,不再逃避现实,而是开始去改变现实”。
我的愤世嫉俗部分来自于我作为一个亚裔澳洲人的身份。我的身体相对而言不太会面临种族暴力的威胁,但在其他方面仍在种族主义的阴影之下。很难知道我能做什么,或者我应该做什么。
但至少,如果我可以把我自己当做鲍德温笔下的“我们”的一份子,并把所有性别身份包括到他所说的“兄弟”一词中的话,我至少可以找到些许勇气,去希望我的愤世嫉俗是错误的。
*以上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